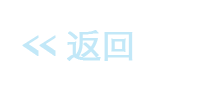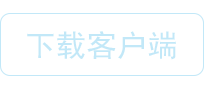全球资本市场的动荡与分化从未停歇,地缘政治冲突、货币政策转向与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交织,迫使国际投资者不断调整资产配置策略。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,中国国债逐渐进入全球视野,成为多元化投资组合中的新兴选项。然而,中国国债的外资持有比例仍显不足。这一矛盾现象的背后,既有中国经济基本面的韧性支撑,也暗含结构性挑战的制约。
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相比,中国的经济基本面具备一定韧性,支撑着国际投资者对中国主权信用的信心,因此中国国债对国际投资者具备一定吸引力。2024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1349084亿元,比2023年增长5.0%,显著高于全球3.2%的平均增速;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(CPI)同比上涨0.2% ,物价总体保持稳定;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4.5%,拉动GDP增长2.2个百分点,最终消费支出明显高于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25.2%的贡献率,消费日益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性力量。IMF在报告中强调,中国“以内需驱动为主的复苏模式,降低了对外部波动的依赖”,增强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主权信用的信心。
与此同时,尽管国债收益率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经历较大的下行压力,但是相对较高的收益率优势在全球低利率环境中具备一定吸引力。2024年初,中国国债收益率还处在比较高的水平。例如2024年3月的时候,10年期国债收益率接近2.6%,虽低于美国4.1%的收益率,但高于德国的2.3%和日本的0.7%。若考虑汇率对冲成本,中国国债对欧元区投资者的实际收益仍具竞争力。更为关键的是,中国央行通过降准、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等手段维持流动性合理充裕,避免债市受到过度冲击。这种“以我为主”的政策框架,为外资提供了稳定的收益预期,成为吸引长期资金的核心因素之一。
政策层面的持续开放则为外资参与中国债市扫除了制度障碍。2017年、2021年“债券通”北、南向通先后启动,此外中国国债先后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(BBGA)、富时罗素世界国债指数(WGBI)等主流国际指数,权重提升至5%-10%,直接带动超千亿美元被动资金流入。2019年9月,中国取消QFII/RQFII额度限制,此后逐步简化跨境资金结算流程;2024年初,财政部进一步优化国债发行透明度,降低外资交易成本。这些举措不仅加速了中国债市与国际规则的接轨,更释放出深化开放的明确信号。
汇率风险的可控性亦是外资持有中国国债的重要考量。2023年,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年化波动率为4.5%,低于新兴市场货币6.8%的平均水平。离岸市场风险管理工具的完善,如香港推出扩大CNH利率互换和外汇期权等人民币衍生工具,为投资者提供了更灵活的对冲手段。国际清算银行(BIS)数据显示,人民币在全球外汇交易中的占比已升至7.0%,稳居第五大交易货币。这一趋势表明,人民币资产的流动性与避险属性同步增强,为外资持有中国国债提供了“安全垫”。
以上因素构成了外资持有中国国债的支撑力量。然而,尽管优势显著,中国国债的外资占比仍远低于美债、日债。2024年,外资持有美债总额约为8.51万亿美元,持有日债总额约1.38万亿美元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各年的《金融市场运行情况》,截至2022年末,境外机构持有国债2.3万亿元;截至2023年末,外资持有中国国债2.3万亿元人民币,与2022年持平;截至2024年末,境外机构持有中国国债2.06万亿元,相比2023年下降10.4%,更加反映出中国国债对外资投资的深层次的结构性挑战。
首先,境外投资者需通过QFII、RQFII或“债券通”渠道参与市场,资金汇出已简化但仍需备案,衍生品交易受限。根据国际清算银行2023年的报告,中国的利率期权、信用违约互换(CDS)等工具尚未向外资全面开放。
货币地位差异同样制约中国国债避险属性的认可度。截至2024年二季度末,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占比达58.22%,而人民币约为2.1%-2.5%。此外,地缘政治风险溢价进一步抑制了外资对中国国债长期配置的意愿。最后,政策透明度不足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。
中国国债的吸引力源于经济增长韧性、收益优势与政策开放红利,但外资配置比例偏低暴露了结构性短板。中国需在资本账户开放、衍生品创新及政策沟通机制上实现突破,方能在全球债市格局中占据更核心地位。对政策制定者,需将短期开放措施转化为长期制度竞争力——唯有平衡风险与机遇,方能在国际资本博弈中赢得主动。(来源:安邦咨询)